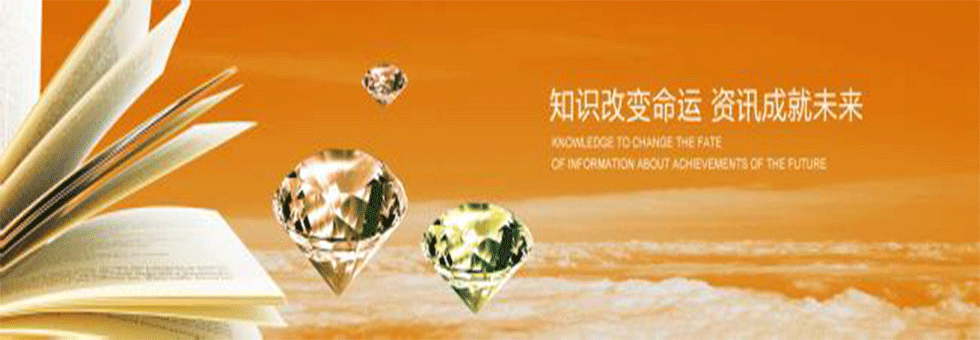
北京中科白癜风在哪里 https://m.yiyuan.99.com.cn/bjzkbdfyy/yyhj/260660/
前言
《万国通史》是官僚阶层与传教士合作的产物,既不能满足求新者的全部需求,又不能帮助守旧者和科举考生,面对激变的时代和呼之欲出的变革无力回应,它的命运最终走向昙花一现。《万国通史》的插图因其丰富性与代表性,成为编撰者的素材库。传教士出版物的插图数量更多,且多采用透视、明暗等现代绘制工艺使之更为精确。
苏特尔《李提摩太传》曾对《万国通史》的影响予以很高评价,认为“这书销售通国,风行一时,以后维新潮流受这史书的动力不在少数”。广学会成立40周年时,统计最畅销之书,《万国通史》亦位列其中。该书实际上对晚清阅读世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首先,它为当时的史地研究者提供参考。李泰棻编写《西洋大历史》曾引用《万国通史》;陶希圣在《穆天子传西征讲疏》中也提到《万国通史》中关于人种的论述;王先谦为撰写《五洲地理志略》托友人缪荃孙购买该书。其次,为科举考生提供备考资源。1901年,清廷宣布科举改制,要求考题中涉及各国政治艺学,考试范围由此大为扩展,包含“工艺学问规制教法”的《万国通史》恰能成为参考书。李提摩太称:“各省的学政们开始从世界史中出题—秀才们不读瑞斯的《世界通史》就答不上来。”
再次,成为部分学校的西洋史教科书。镇江女塾为学生在第十、十一年开设“读万国通史课”。甲午战争前,各教会学校、外语学校就已零星开设世界史课程,并使用相关译著作为教材。此后,更多新式学堂教授世界史。1902年,《钦定中学堂章程》将“中外史地”和“與地”安排至中学课程中,虽未施行,但足见官方之重视。次年,《奏定中学堂章程》进一步明确世界史课程。为满足学堂对世界通史的需求,广学会向“中学以上各学校及各地图书馆”赠送《万国通史》。《万国通史》丰富的插图被当时不少历史出版物所转引,如秦瑞玢的《高等小学西洋历史教科书》、傅岳棻的《西洋历史教科书》、傅运森的《西洋史》和余协中的《西洋通史》。在晚清影响颇大的《迈尔通史》也从《万国通史》取用插图,埃及部分用八张,巴比伦尼亚部分用四张。以卡尔纳克神庙圆柱为例,《大学尚中世界通史》插图以照片形式呈现,而《迈尔通史》则是绘画,脱胎于《万国通史》,甚至连右下角的裁剪都丝毫不差。
正如蔡尔康所言,蕲合左图右史之古谊尤为藻不妄抒”,这些精确的现代插图既契合了我国左图右史的传统,更便人们认识到史书插图的意义,郑振铎由此感叹史书中诸多方面“都是非图不明的'《万国逋史》既为研究者提供世界史知识,又在学校教育,科举考试中,发挥相缉作用,插图还被其他历史作品借鉴,其受众面应该很广,然而实际形恐非如此。相较于其他流狩的传教士史著,影响有限“不甚畅销,以致广季会颇受赔累”。在发行量上,据广学会年报载,该书共印刷2000册,同年《中东战纪本末三編》发行2500册,之后也再来重印。据《晚清营业书目》,民臂书見中《前编》仅在上海申昌书局有售,外界对《万国邋史》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前者,后者却鲜被提及。总体而言,《万国通史》绝未如中东战纪本末等般流行。在教育方面,前文提及,国人开始编译西洋史教科书,出现更适合争堂的教材,而洋洋洒洒30卷的通史令人塑而生畏。在译著中,冈本监辅《万国史记》吏得新式學堂青睐,如湖南时务学堂、天津育才馆等,都采用这部:史书。该书在晚清之盛可谞“翻印不知若千次,读书人大概人手一编广受欢迎的西学时务类考试用书是侧务通考顧学大成》等汇编,知识纖史书更广,更适合考生针对广学会统计的暈畅销之书,王树槐指出,这些书大都“并非由宁销售而出版,多由于赠送而印行李提摩太主观上重视《万国通史自然多多印刷赠与官绅,但未必能达到预期效果。为何这部详虐且具針对性的箸作未能如广學会期待般产生较大影响呢?
首先,《万国通史》内容冗杂,价格昂贵。30卷的规格造成阅读负担,原本优质的著作“因为卷帙太多卖的人反而少了。相较之下,该书更适合研究者参考,如前文提到的陶希圣、王先谦‘货笔烦冗“过于润色,致失:原书本寞堆积的辞藻直镔巌响阅:读体验。张元济评价该书“搜辑甚賞,而文字太劣。价格上,该书为18.2Cmx30.4她大开本豪华线装书成本较高《广学会译著新书总目前编》售价3范角,续编和补编售价5元,较广擎会其他出版物实属昂贵。该书在韦爲寄售曲价格更:居高不下,在美华书馆、申报馆和申昌书局均定价6元,而《万菌通鉴》在申昌书局仅售1元,《万国史记》仅售8角。总之,《万国通史》的篇幅、价格、译笔等都使一般士人望而却步。其次,从书目角度看,《万国通史》出版较晚,未能被诸如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叶瀚的《初学宜读各书要略》和《初学稍进读书要略》等为时人提供读书门径的西学目录书收录,或也局限了知名度。《申报》的“考试时务场中必备书”广告中,《万国通史》不见踪影。面对纷繁的西书,读者自会优先参考学者和报刊推荐书目。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译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广学会失去了竞争力。张之洞“译西书不如译东书”—语更反映时人主张师法日本、编译东籍。《万国通史》不仅在西书中受到冷落,还受到东书的冲击。最后,取士标准与时人的心理趋向也影响西书市场。并非改革政令颁布后,便马上激起广大士人对西史的热情。实际上,对中下层士人而言,经史仍是阅读主流,取士标准仍延续明代“重首场”的现象。李提摩太虽言士人不读《万国通史》就不能答题,但对考生而言,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论”对科举成绩没那么重要。评卷时,考官也并不希望答卷观点太新,因为这往往会违背清廷中体西用的初衷。《中外日报》曾揭示改革后的情形:“惟近来由考试中显明,国家之本旨,仍以守旧为重。因考试之文,凡见解少新者,均不获售;而意思极旧者,反蒙录取故也。”这一时期的取士似新实旧,取高分的关键不在于新学。这就直接影响到书籍市场,西书在考市中并不好卖。考官对西学尚持如此观点,整个社会更与西学产生隔膜。王维泰在《汗梁卖书记》中把购买《朔方备乘》《泰西新史》等西书的考生划为中下乘。在保守的心态下,西书在民间举步维艰。结语《万国通史》博采外国史著,迎合时人对世界知识的渴求。该书在线性历史观下,追寻人类起源,探究文明演进的历史,以“工艺学问规制教法”的进步历程为公例,描绘一幅欧美主导下的世界图景。在“居今以稽古”的宗旨下,李思伦白向统治阶级提出诸多治国建议,契合传教士的意图。
《万国通史》影响虽有限,但暗合彼时新史学思潮。其一,该书较早将西方考古成果引入中国,系统介绍了史前三期说和地层学的方法,为中国史界带来新气息。其二,李思伦白强调“工艺学问规制教法”的文明史,与新史学的“民史”主张相通。其三,《万国通史》的线性历史观冲击了旧史的循环观念,与史界变革产生共振。从梁启超提出史学应“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到国人自编的历史教科书多充满了社会进化、历史分期等观念,线性历史观逐步在中国得到接受。然而,对于万物何以进化,李思伦白归因于宗教。这是传教士著作的通病,谢卫楼《万国通鉴》反复宣扬真主创造天地万物,丁韪良《西学考略》认为万物的进化能力来自“大造之命”,李提摩太更直言广学会最大目标就是传教,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提供给中国所需要的新道德的动力”。《万国通史》的另一局限在于它更多反映官僚阶层的愿景,书中提倡的诸多改良政策皆正中他们下怀,却与整个社会产生隔阂。在社会层面,相较于欧洲历史,此时的求新者更欲了解与中国经历相似的日本何以崛起,而《万国通史》对此没有回应。
结语
一般读者渴求带领西方步入强国之列的社会科学理论,该书没有提供此类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