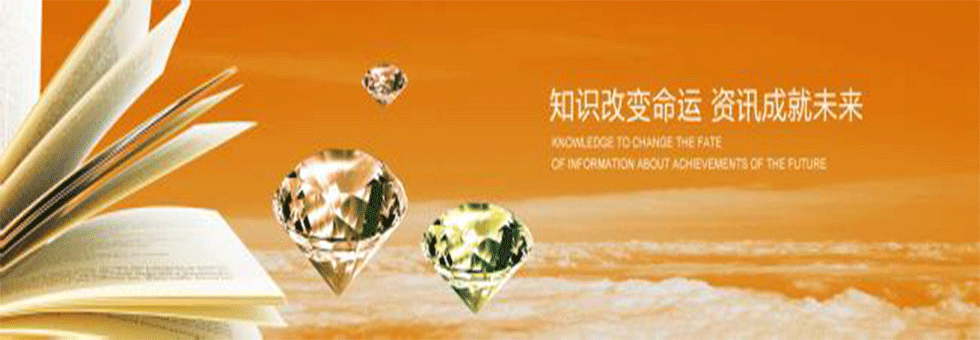
今天转载两篇文章,是鲁迅先生的《作文秘诀》,以及易中天老师的《书要怎样写?才会有人读!》。鲁迅先生作文的那个时代,配图和照片还是一个高级活,所以先生的文章主要是犀利的文字。易中天老师在自媒体时代坚持写书,为了打开销路,要把书整得图文并茂,而且还要配清爽的图。在两位大师面前,说什么都是多余的,直接上文:
鲁迅先生雕塑现在竟还有人写信来问我作文的秘诀。
我们常常听到:拳师教徒弟是留一手的,怕他学全了就要打死自己,好让他称雄。在实际上,这样的事情也并非全没有,逢蒙杀羿就是一个前例。逢蒙远了,而这种古气是没有消尽的,还加上了后来的“状元瘾”,科举虽然久废,至今总还要争“唯一”,争“最先”。遇到有“状元瘾”的人们,做教师就危险,拳棒教完,往往免不了被打倒,而这位新拳师来教徒弟时,却以他的先生和自己为前车之鉴,就一定留一手,甚而至于三四手,于是拳术也就“一代不如一代”了。
还有,做医生的有秘方,做厨子的有秘法,开点心铺子的有秘传,为了保全自家的衣食,听说这还只授儿妇,不教女儿,以免流传到别人家里去。“秘”是中国非常普遍的东西,连关于国家大事的会议,也总是“内容非常秘密”,大家不知道。但是,作文却好像偏偏并无秘诀,假使有,每个作家一定是传给子孙的了,然而祖传的作家很少见。自然,作家的孩子们,从小看惯书籍纸笔,眼格也许比较的可以大一点罢,不过不见得就会做。目下的刊物上,虽然常见什么“父子作家”“夫妇作家”的名称,仿佛真能从遗嘱或情书中,密授一些什么秘诀一样,其实乃是肉麻当有趣,妄将做官的关系,用到作文上去了。
那么,作文真就毫无秘诀么?却也并不。我曾经讲过几句做古文的秘诀,是要通篇都有来历,而非古人的成文;也就是通篇是自己做的,而又全非自己所做,个人其实并没有说什么;也就是“事出有因”,而又“查无实据”。到这样,便“庶几乎免于大过也矣”了。简而言之,实不过要做得“今天天气,哈哈哈……”而已。
这是说内容。至于修辞,也有一点秘诀:一要朦胧,二要难懂。那方法,是:缩短句子,多用难字。譬如罢,作文论秦朝事,写一句“秦始皇乃始烧书”,是不算好文章的,必须翻译一下,使它不容易一目了然才好。这时就用得着《尔雅》,《文选》了,其实是只要不给别人知道,查查《康熙字典》也不妨的。动手来改,成为“始皇始焚书”,就有些“古”起来,到得改成“政俶燔典”,那就简直有了班马气,虽然跟着也令人不大看得懂。但是这样的做成一篇以至一部,是可以被称为“学者”的,我想了半天,只做得一句,所以只配在杂志上投稿。
我们的古之文学大师,就常常玩着这一手。班固先生的“紫色鼃声,余分闰位”,就将四句长句,缩成八字的;扬雄先生的“蠢迪检柙”,就将“动由规矩”这四个平常字,翻成难字的。《绿野仙踪》记塾师咏“花”,有句云:“媳钗俏矣儿书废,哥罐闻焉嫂棒伤。”自说意思,是儿妇折花为钗,虽然俏丽,但恐儿子因而废读;下联较费解,是他的哥哥折了花来,没有花瓶,就插在瓦罐里,以嗅花香,他嫂嫂为防微杜渐起见,竟用棒子连花和罐一起打坏了。这算是对于冬烘先生的嘲笑。然而他的作法,其实是和扬班并无不合的,错只在他不用古典而用新典。这一个所谓“错”,就使《文选》之类在遗老遗少们的心眼里保住了威灵。
做得朦胧,这便是所谓“好”么?答曰:也不尽然,其实是不过掩了丑。但是,“知耻近乎勇”,掩了丑,也就仿佛近乎好了。摩登女郎披下头发,中年妇人罩上面纱,就都是朦胧术。人类学家解释衣服的起源有三说:一说是因为男女知道了性的羞耻心,用这来遮羞;一说却以为倒是用这来刺激;还有一种是说因为老弱男女,身体衰瘦,露着不好看,盖上一些东西,借此掩掩丑的。从修辞学的立场上看起来,我赞成后一说。现在还常有骈四俪六,典丽堂皇的祭文,挽联,宣言,通电,我们倘去查字典,翻类书,剥去它外面的装饰,翻成白话文,试看那剩下的是怎样的东西呵!?
鲁迅先生雕塑不懂当然也好的。好在那里呢?即好在“不懂”中。但所虑的是好到令人不能说好丑,所以还不如做得它“难懂”;有一点懂,而下一番苦功之后,所懂的也比较的多起来。我们是向来很有崇拜“难”的脾气的,每餐吃三碗饭,谁也不以为奇,有人每餐要吃十八碗,就郑重其事的写在笔记上;用手穿针没有人看,用脚穿针就可以搭帐篷卖钱;一幅画片,平淡无奇,装在匣子里,挖一个洞,化为西洋镜,人们就张着嘴热心的要看了。况且同是一事,费了苦功而达到的,也比并不费力而达到的可贵。譬如到什么庙里去烧香罢,到山上的,比到平地上的可贵;三步一拜才到庙里的庙,和坐了轿子一径抬到的庙,即使同是这庙,在到达者的心里的可贵的程度是大有高下的。作文之贵乎难懂,就是要使读者三步一拜,这才能够达到一点目的的妙法。
写到这里,成了所讲的不但只是做古文的秘诀,而且是做骗人的古文的秘诀了。但我想,做白话文也没有什么大两样,因为它也可以夹些僻字,加上朦胧或难懂,来施展那变戏法的障眼的手巾的。倘要反一调,就是“白描”。
“白描”却并没有秘诀。如果要说有,也不过是和障眼法反一调;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
十一月十日。
易中天老师(来源网络)书要怎样写?才会有人读!
易中天在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现场讲有句老话,叫:“看书只看封皮,看报只看标题。”这话原本是讽刺不认真学习的。但,如果换成这样:“看书先看封皮,看报先看标题。”那就是正常的阅读心理了。
其实,读书就像恋爱,难免以貌取人。如果是到图书馆借阅也就罢了,打算购买或收藏就不会不看封面,换了我还要看手感。所以呢,有些道道还是得讲讲。
1、封面要清爽
封面就是脸面。脸面必须清爽。比如:
康德著,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这个封面庄重大方,简洁高雅,特色鲜明,信息传达准确,让人爱不释手。又比如:
易中天著,胡永凯图,付诗意设计,上海如果设计成这样呢?
来源网络就叫俗不可耐。再比如:
易中天著,朱镜霖设计,浙江文艺出版社如果设计成这样呢?
来源网络就叫惨不忍睹。长成这样,还能给人好印象?印象都不好,你还指望人家跟你交朋友?当然,必须说明:“清爽不等于素雅,而是不能艳俗。”比如这个封面,就浓墨重彩:
鲁迅编,林林设计,三秦出版社这样的设计,也叫清爽。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封面也一样,可以眉清目秀,也可以浓眉大眼,还可以熊腰虎背,但不能歪瓜裂枣,獐头鼠目,卖弄风骚,或者邋里邋遢。那就叫脏。脏,是审美的大忌。
不过,封面如何,是出版社的事情,作者一般管不着。作者能咋样呢?也有三点建议。
2、学做标题党
标题很重要吗?当然。封面就像脸,标题就像眼睛。看一个人的眼睛,就可以知道他是什么人。同样,看书名,可以知道这是什么书。可惜,不少作者似乎不太在意自己的眉眼。常见的有以下几种:“自作多情”。举个例子吧!比方说,有位民营企业家在美国打官司,而且胜诉了,回来出本书,该叫什么名呢?有三个选项:我们赢了,分享我的胜利吧,在美国打官司。
请问,该选哪个?第一个最不好。什么叫“我们赢了”?言下之意是:他们输了。其实,民事诉讼就像竞技体育,总会有输赢。赢了没啥了不起,输了也不多丢人,有什么可说的?更何况,胜败乃兵家常事。如果赢了就得瑟,只能说明你从没赢过。掉价不掉价,跌份不跌份啊!实在忍不住,也得改成:“谢谢你让我们赢了”,就像武林高手赢了以后说声“承让”那样。这才有风度。不过,名叫《承让》的书,也未必有人看。
分享我的胜利吧,同样不好。你的胜利,我为什么要分享?我是你爹,还是你娃?这叫什么呢?典型的自作多情。包括第一个书名,也是。
作者应该想想,你的输赢,关读者什么事?不关他的事,他又为什么要看?必须牢牢记住:书名和标题是为读者起的,不是为自己。所以,硬要拿输赢说事,那就不如改成:我们差点输了。这个书名,为什么又可以呢?因为你的输赢虽然不关读者什么事,但是“差点输了”却能引起好奇心。什么事情差点输了?差点输了的又怎么会赢?我们能从“差点输了”的事情中得到哪些教训?总之:有关联度和代入感。读者才会感兴趣。自作多情,就会不知所云。
我就犯过这样的错误。年,我出了本书,叫:《艰难的一跃》,这个书名为什么不好?因为读者根本不知道你要说什么。什么叫“艰难的一跃”?谁跃?从哪跃到哪?不会是跨栏吧?跟我有啥关系?当然,这本书是有副标题的,可以回答前面的问题。但是,有多少人会耐心再看副标题呢?往往在发现副标题之前,他们已经抛弃你了。总之,我那本书的结果,是几乎无人问津。
由此得出结论:不知所云的书名再加上解释性的副标题,是最不好的命名方式。当然,不是说绝对不能正副标题并用。前提是,主标题必须有吸引力。比如:《东往东来__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
陈力卫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这个书名为什么就好呢?因为新奇,而且有悬念。相反,自以为诗意盎然的,往往不好。比如《中华史》第一卷的书名,原本叫做:《黎明时分》,交稿以后,果麦公司董事长路金波马上表示反对。他问:“你这是小说还是诗?有谁知道这本书的内容是什么吗?”然后他又说:“书名就像路牌,功能是指明方向。”于是,我将书名改成:
来源网络结果,该书累计印刷75万册。我说《在美国打官司》比较好,道理也在这里。
只会套路。这方面例子很多。比方说,我们会在网上看到这样的标题:面对质疑,某某一句话回答亮了。相同的还有:懵了,怒了,崩溃了,悲剧了,总之,都是这种套路。有问题吗?没有。有意思吗?也没有。呵呵,昨天刚亮过,今天又亮了,你是灯泡么?总有一天,读者会烦。
故作惊人。许多年前,某报发表了一则消息,标题是:易中天加盟好男儿。这当然是假新闻,但他们加了个副标题:正在积极联系中。但是请问,有谁注意到那行小字呢?我却无话可说,因为人家可能确实在“积极联系”中,只不过联系不上。这就是故作惊人之语了。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结果,标题党成了贬义词。其实不然。多年前《解放日报》曾经约我写城市专栏,我写了篇西安的,标题叫:秋风渭水长安。出典贾岛的诗:“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所以,写好以后,我自鸣得意。副总编辑王富荣先生看了后却认为不好,便从文章中挑出一句话做标题:秦腔是西安人的足球。大家说,是不是好了很多?标题党,是不是可以学习?
3、写好第一句
好的作家,都在乎第一句。比如浩然《艳阳天》的开头:萧长春死了媳妇,三年还没有续上。还有铁凝《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我和妹妹喜欢在逛商店的时候聊天。实话实说,看到这些第一句,就想读下去。而且,直觉告诉我,他们是好作家。不过,真正把我镇住的,是这一句:点是没有部分的东西。第二句也很牛:线是没有宽的长。这是哪本书里的?
张卜天译,江西人民出版社作者是谁?欧几里得。
来源网络为什么这两句话镇住我了呢?因为想不出更好的表述方式。的确,点,不管画多大,都是一个整体,没有构成部分。线,也不管多粗,宽都没有意义。精准啊!正是这种精准,表现出《几何原本》独有的气质:理性,严谨,冷峻。这种气质,非常迷人。男人有这种气质,女人会着迷。著作有这种气质,男人会着迷。
每个作家和每部作品都有自己的气质,好的作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第一句就表现出来,比如铁凝的那句话:我和妹妹喜欢在逛商店的时候聊天。如果改成:我和妹妹逛商店的时候,喜欢聊天。那就不是铁凝的气质了。所以我自己,也特别重视第一句。比如《中华史》第十卷《三国纪》:汉灵帝死后的洛阳,满城都是杀气。我这样写,是想在第一时间就把读者带入历史现场,并且强烈地感受到那个动荡不安时代的氛围。这也是一种气质。可以说:封面是脸。标题和第一句是眼睛。它们的风格是眼神。眼神可以有多种,但决不能飘忽不定。即便不能光彩夺目,至少也别让人生厌。毕竟,作者与读者需要交流。
4、内容别撒谎
最重要的,是内容。内容才是决定性的。这就好比一个编剧,如果只是不断地设置悬念,却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和结果,观众肯定要愤怒。
在这里,请允许我说一句重话:标题耸人听闻,内容空洞苍白,是诈骗犯!还有:开头漂亮引人,后面并不入胜,是耍流氓!始乱终弃嘛!
结论。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书要怎样写,才会有人读?四句话:封面要清爽,学做标题党,写好第一句,内容别撒谎。
总之,我个人的经验是:写作的目的本在传播。拒绝或者不屑于掌握传播规律和技巧,恐怕会死得很难看。
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已经过去,庚子年即将到来。值此辞旧迎新之际,我衷心祝愿诸位都能写好自己的第一句,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和圆满的结果!
谢谢大家!
读了以上两篇文章,受益匪浅!
(特别声明:以上文章和图片来源网络,最初的起点还是鲁迅先生和易中天老师。)